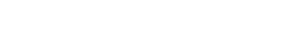5月10日周日《解放日报》的“思想者”专栏全文刊载了陈伟恕教授在我校所做演讲内容。
以下为发表的全文。
世界新秩序的曙光与阴霾
――
近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入及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的两度召开,关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议题,成为全球热门话题。各国政要、学者专家和民众大都从各自的利益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这场讨论的意义何在?我想,主要有两条:第一,我们要看清世界新秩序演变的大致趋势及其可能遭遇的曲折;第二,要看清中国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的角色选择。此外,我相信,通过对这个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与探讨,我们民族与人民自身的思维理性和战略自觉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世界秩序是一个宏大叙事的国际政治概念,专指一系列具有现实性、合理性、稳定性,且获得国际间共识、共享和共同遵守的原则与规则的结构框架。在世界上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拥有最高权力的“世界政府”的情况下,世界秩序一般表现为一系列的国际公约和国际组织,在人口、资源、经济上合起来占世界上压倒性比重的众多国家的参与,以及由一个或几个主要国家来扮演领导者或主导者的角色。在上述三种表现形式中,第三点尤为重要。
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曾分别由不同的大国主导形成不同的世界秩序。一个大国能否成为世界秩序中的主导性大国,主要取决于六个要素:第一,“实力”―――不仅具有强大的综合基础国力,还能引聚出正向的国际合力;第二,“价值”―――奉行有生命力的、能鞭挞时代非正义力量的、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第三,“目标”―――具有合理、主动的充当世界引领者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第四,“组织”―――拥有具备巨大潜能的迅速动员能力和有效的行为体系组织能力;第五,“途径”―――掌握正确的、能够有效实施的战略策略;第六,“机遇”―――能够善于利用偶然出现的机遇,并作出及时而恰当的反应。
以此来看,世界秩序中的“旧”与“新”总是相对而言的,由旧到新,永远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渐进的、甚至是曲折的演进过程,且新旧秩序之间从来不存在绝对的时间界线,只能从历史的角度选定一个标记性的时间作为分界。也因此,任何具有现实意义的关于世界新秩序的讨论,一定要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下。
对新秩序的界定
随着此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不断蔓延和深化,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旧”秩序正从其内部开始崩塌。这种秩序的瓦解主要是由美国自身的行为导致的。
当前,我们所谓世界新秩序的“新”,主要是针对现有世界秩序中的“旧”而言的。这个“旧”的核心问题就是以美国为“中心领导者”的世界秩序。它具体由几部分构成:第一,由布雷顿森林会议所确定的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及由美国所主导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国际组织;第二,以由美国牵头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其主要标志是G7会议制度;第三,以美国为首的军事体系,包括北约组织、美日军事同盟等,也体现为美国发动的一系列局部战争,作为维系这一秩序的强制手段;第四,所谓“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鼓吹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文化模式以及生活方式。
然而,随着此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不断蔓延和深化,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旧”秩序正从其内部开始崩塌。这种秩序的瓦解主要是由美国自身的行为导致的,这些行为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金融无政府主义。美国假全球化、自由化之名,要求各国实行全面的金融开放,以便于其以金融寡头资本为核心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评估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展跨国经营活动。正是在美国的推动下,全球经济出现了过度虚拟化的格局,金融业屡屡以“衍生工具”、“金融创新”为幌子,肆无忌惮地攫取超额利润。随后,在持续的阵发性的大小金融危机中,各国、各地区、各阶层的财富被一批批吮吸而去。面对这种金融无政府主义,美国政府及其金融当局是放任的、熟视无睹的,而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则无能为力、束手无策。
美国政府在经济上的错误政策。二战后,美国一直仰仗美元的特殊地位,不负责任地滥发货币。一方面通过贸易逆差来搜罗世界各地的资源、产品和人才,而使别国获得不断趋于贬值的美元资产;另一方面又不断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和财政赤字来强化本国的科技进步、军备扩充和社会安定,而使别国难有选择地购买并持有正在走向贬值的美元债权。在这种抵赖式的“负债经济战略”下,不仅政府,而且几乎所有企业、家庭和个人,都沉溺于“寅吃卯粮”的生存方式中。而这次次贷危机,也是美国过去几届政府奉行“居者有其屋”政策,而美联储又持续放松银根,相关金融监管、评估机构又玩忽职守的结果。整个社会这种积重难返的、不讲信用的负债恶习,早已为一场大危机埋下了祸种。
美国在国际关系上的霸权行径。美国对外高举“民主”、“自由”、“人权”大旗,却常常奉行有所选择的双重标准,几乎不间断地挑起或参与一场又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而这不仅由于需要庞大的军备开支来维持而逐渐耗损了美国内在的基础性国力,也使美国在国际上丧失了凝聚人心的人道主义信誉。
美国主流意识形态陷入两条歧途。近三十年来,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尚未对此作出深刻反省和全面调整,还继续在两条歧路上彷徨。一条是在政治意识上,美国仍在崇尚帝国意识、对抗意识、冷战意识和军备第一意识,继续执意推行美国式民主制度;另一条则是在经济意识上,仍然贯彻增长至上、市场至上、效率至上和财富至上的社会意识,不愿在全球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和消除贫困方面,承担起作为领导者应尽的建设性责任。
当然,尽管上述分析表明,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和世界旧秩序瓦解的主要根源来自于作为其内在核心的美国本身,但除此之外,任何参与旧秩序之中并获得一定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国家都与此脱不了干系,推诿各自的相应责任也是不应该的。全球各国都需从中反思和反省,走向进一步的自我变革与调整。
曙光还是阴霾
未来三十年的世界新秩序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基本和谐的、正当的、以正义为主导的“光明新秩序”。而另外一种则可能截然相反,基本冲突的、非正常的非理性将占据上风。
从更深刻的背景来看,旧秩序之所以可能瓦解,也是因为世界的现实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并出现了产生新秩序的历史必要性和可能性。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全球化是在旧秩序下展开的,但也发展到了它的转折关口。这体现在,第一,尽管由于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的相互关联已越加密切,但各国都不约而同地遇到了能源、环境、气候、贸易和经济平衡等全球性问题。第二,以往的全球化,一使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各国国内社会的中下层民众遭到了冷漠与掠夺,二让不同文明及其价值观面临不平等的对待。然而,对于这些旧秩序的产物,一来不可能在旧秩序中得到解决,二则至今缺乏解决问题应有的理念和机制。
其次,世界经济力量的重心发生了转移。特别表现在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力量的上升,巴西、南非和俄罗斯等大国经济力量也重新显现。以往“中心―边缘”的世界经济格局理论已失去说服力。现在的情势是,在经济上,中美互为彼此依存的伙伴,发达经济和新兴经济相互平衡、互为制约,双方都不可替代。经济全球化已造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
第三,各国国家力量的运用面临新的困惑和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因素:全球问题与国内问题相互之间既牵引又冲突;各种非传统威胁接踵而至;非政府组织形形色色,良莠不齐;互联网使公民自主行为意识兴起;人口、资源、信息和财富的跨国转移和越界交融等。这都意味着,国家行为在对上、对外的方向上,有一个国际协商协作而使主权淡化与共享的问题;在对内、对下方向上,对于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有一个既允许一定程度的自治与自主,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统一规范与大局稳定的问题。
由于以上历史性转变的出现,世界正需要一种新秩序来适应和框定国家力量有效运用的新格局。可以预计,未来的30年,将是酝酿世界新秩序最具不确定性也最有希望的时期。也就是说,有曙光,也有阴霾,既可能取得企盼中的结局,又可能得到谁也意料不到的后果。我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在我看来,新秩序的曙光即将或已经显露在:
改革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几成国际场合的热点议题,并将被逐步提上相应的议事日程。就目前的讨论来看,未来国际货币制度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美元、欧元、日元和人民币组成一揽子货币,各国按比例搭配;第二,建立新的超主权货币,其定价基础有多种方向选择;第三,仍以美元为中心,但是美元发行机制受到国际公约约束。不管何种可能性,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都会明显地逐步增强,亚洲地区的货币和金融合作也将显现。
G20会议制度的形成和不断完善。今后讨论世界经济问题将可能以G20为平台,并由此拓展出多层次多领域的全面对话协商机制,并有可能逐步产生更多具有专业性约束力的经济合约。
新型的国家间军事合作公约和联合行动开始盛行。对于那些执意违约的侵犯全球公共利益的重大行为,如破坏国际正常的运输和网络通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恶意制造的大规模环境破坏等,需要国际间的联合军事行动。
近来西方提出的“北京共识”,不论这种提法准确与否,都表明国际思潮正在发生变化。政府作用、东方理念、社会主义观念、人类共同体意识都将更受关注,而中国所实施的那种能够使社会持续发展、具有相当稳定能力并以和谐为宗旨的单一政党领导、多党合作制的国家治理模式,将逐步被国际社会正面地理解和接受。
然而,新秩序的阴霾同样存在:全球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会在一定程度上死灰复燃,经济摩擦纠纷更加频繁,可能引起一系列的“货币战”、“贸易战”、“资源战”和“投资战”,导致更多的外交纠纷和政治危机;欧美社会深藏着一股代表垄断集团利益的精英联盟试图幕后掌控世界的政治势力,如美国的极端右翼保守主义,很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东山再起;世界各地非政府的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可能进一步抬头,借助宗教信仰、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不公或环境恶化等公共话题,煽动和组织无政府主义或反政府主义的暴力动乱,以乱中求利、火中取栗;不少陷于经济困境的国家内部容易滋生狂热的民族主义、过激的民粹主义思潮,并可能通过民主普选的政治领袖的偏执行为来加以宣泄,由此将带来长期性的国内动荡和国际冲突;气候突变、重大地质灾害、意外失控的核武器或生化武器的爆炸以及突发的灾难性粮荒、油荒或恶性传染疾病,可能会具有全球性影响,迫使尚有能力采取抗击的国家力量应急地采取某种临时性措施,从而有可能路径依赖地成为长期性的制度安排,并同预期中的新秩序大相径庭。
基于以上分析,未来三十年的世界新秩序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基本和谐的、正当的、以正义为主导的“光明新秩序”。而另外一种则可能截然相反,基本冲突的、非正常的非理性将占据上风。现在前者是主流,后者只是支流、潜流,但是不排除逆转的可能。事在人为,我们应该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促成“光明新秩序”。
中国的角色定位和战略选择
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应采取的基本态度是“强体蓄能,顺势而为,把握主动,巧应利导”。只有在此认识基础上,中国才能在朝向基本和谐的、正当的世界新秩序的进程中扮演好自己的战略角色。
在此背景下,对于我国而言,有两种偏执的情绪是需要避免的。一种是无所作为地独善其身,消极地理解和对待“韬光养晦”的策略;另一种是妄自尊大、盲目冲动的民族主义,不明智地去争抢所谓的主导权,或者不必要地摆出针锋相对的架势。我们应当理智而又清晰地定位中国在世界新秩序形成过程中的角色,应当有这样一些基本认识:要全心全力地把办好中国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与此同时承担起相应的、适当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在解决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时不能相互割裂开来,要注重兼顾和互动。
在未来三十年的新秩序演进中,我们还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也不能充当中心和领导者。但是,我们要逐步有序地、不失时机地扩大影响力。这是一种崭新面目的影响力,而不是旧式帝国或霸权的影响力。在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间找到和谐的、双赢的途径,是一条需要我们长期探索的道路。
我想,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应采取的基本态度是“强体蓄能,顺势而为,把握主动,巧应利导”。只有在此认识基础上,中国才能在朝向基本和谐的、正当的世界新秩序的进程中扮演好自己的战略角色,成为一个积极而适当地、权责利相一致的、逐步扩大影响力的主动参与者。
那么,具体而言,中国在迈向世界新秩序的进程中应做好哪些战略选择?我有如下几方面的意见可供大家讨论:
要将国内问题的解决提升到“在全球意义上作出探索与表率”的高度来看待。在经济上,要解决人口增长与老化之间的不平衡问题、探索资源有限条件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在政治上,要创建出一种既能保障社会持久安定,又能不断变革创新、充满活力、提高效能的新型社会治理结构;在策略上,则应加紧增强自身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组织力和国民素质等方面能够产生长期影响的战略威慑力量,致力于形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态势。中国的成功,将具有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国际示范意义。
全方位地同世界各国建立战略合作框架。其中的中心问题是美国,要善用其力、善待其变,对其垄断集团掌握的霸权力量如何避其锋芒而为我所用,也要予以深思慎虑。中美需要联手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与此同时,也务必要处理好同欧洲、俄罗斯、印度、日本等重要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同周边国家及利益关系重大的地区国家,则要建立和睦相处并予以适度援助的稳定关系。对其他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在尚未侵犯我国核心战略利益之时,始终坚持中立、公义和促进和解的立场,保留进一步扩大中国主动影响力的行动空间。
在亚洲地区,我们要有耐心和宽容心,逐步从经济一体化市场扩大到政治、外交甚至军事机制上的合作,这是我国运用力量的必要基础。
在价值观方面,我们要有新的综合和创新,结合当今时代条件,针对全球化人类共同面临的基本问题,将东西方的精神财富加以进一步的提炼整合,塑造一种全人类普遍接受的新的基本价值观。中国要有自信心、决心和恒心,成为凝聚全球人心的既传统又创新的价值观引领者。
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为避免因突发事故而使世界秩序失控并误入歧途,中国有必要加强应对全球性重大突发冲突与战争的基础准备和应急预案,并善于利用这种机遇为世界新秩序的开拓创造条件,并为此作出战略策略部署上的必要准备。
学术界要研究开发一门新的学科―――全球治理学。全球体系应被看作一种自我组织的、自我生长的自然体系,它涉及到人与人、国与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还涉及各种行为主体扮演什么角色、如何保持良性互动与和谐等问题。归根到底,是一门关于制度安排和角色协同的学问。这种治理学既是知识传授体系,也是能力训练体系,它将跨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和意识形态的藩篱。中国现在应该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树立与时俱进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知识体系,积极地影响全球。
中国最终能否在世界新秩序的形成过程中成为国际间众望所归的影响力量,将取决于中国在国内能否保持全面持续的进步和对国际事务的得当处理,而这一切又取决于国家、社会治理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崇洋媚外地照搬西方是不对的,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也不可取,我们需要真正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有序实施。中国人应有这样的豪迈气概:让自己所创造的人类财富、所建立的社会形态、所锤炼的精神品质,真正赢得全世界的认同和仰慕。 (演讲时间:
(《解放日报》电子版链接:
http://epaper.jfdaily.com/jfdaily/html/2009-05/10/node_9.htm)
(国关院)